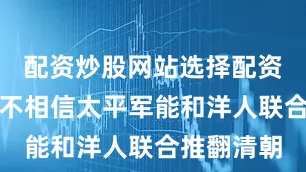
安庆与杭州,在太平军与湘军对战的背景下形成了强烈对照。
1861年冬天,曾国藩攻克安庆后不久,李秀成率部在浙江攻城掠地。顺着长江漂流而下的浮尸群,无言地陈述着安庆的暴行。
然而,比起湘军旷日持久的围攻、破城之后的疯狂屠杀,太平军攻破杭州的过程既轻松,也克制。李秀成有意争取民心,入城之后约束军队,尽量不烧杀抢掠。人们不由得纳闷起来:“豺狼也,岂尚有人心哉?”
接着,李秀成剑指宁波——又一个涉及洋人利益的通商口岸。英国人连忙警告李秀成,不要靠近宁波,离上海远一些。
与洪仁玕不同,李秀成并不相信太平军能和洋人联合推翻清朝,只是天京那边一直阻止他胡乱动武。但这阻止不了他的攻势,太平军继续东进,轻松攻克宁波,进逼上海——依然没有大开杀戒,也没有破坏洋人的财产。
对于中国这场内战,英国议会的态度是保持中立,吓唬太平军,使其远离通商口岸,除非英国人性命受到威胁,否则绝不开战。但英国在华官员却不认同议员老爷们的天真想法:清军看起来太弱了,无法镇压这场叛乱,太平天国要是赢了,很可能导致英国对华贸易停摆。
当硝烟逐渐逼近上海郊区,英国人迅速撕掉冠冕堂皇的“中立”大旗,迫不及待插手到中国的内战之中。
展开剩余95%外国势力,已然是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。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证明,以皇权为中心的天朝体制,无法应对外来的冲击。1861年3月,北京设立总理衙门,负责外交,实际上兼管通商、国防、关税、军工、情报、留学生等事务。与其说是外务部,倒不如说是内阁。11月,辛酉政变,慈禧执政。在她的支持下,总理衙门首脑奕䜣将权力伸展到军机处,并拥有议政王的头衔。
在新体制下,谁能更好地处理涉外事务,谁就能扶摇直上。
1曾国藩拿下安庆后,将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,慢慢收紧对太平天国的绞索。曾国荃把安庆周围清理了一遍,接着大摇大摆回到了家乡,吃吃喝喝,挥金如土,顺道招募了六千新兵。大批新人的加入,继续败坏着湘军的军纪,使其沦为像绿营那样的兵痞队伍。为了消灭天京城内的邪魔,曾国藩需要这群魑魅魍魉。
1861年冬天,江浙来人,请求救援。在此之前,江浙官绅全力支持江南、江北大营,不让湘军插手江南,双方多有龃龉,恩怨几乎不可化解。如今,江浙尽归太平军,只剩下上海一座孤城,他们不得不乞求曾国藩的保护。
曾国藩一开始并未答应。他认为:“上海东北皆洋,西南皆贼,于筹饷为膏腴,于用兵为绝地。”但由于手头的军费见底,他还是改变了想法:“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,不忍坐视其沦陷也。”他本想让曾国荃带兵东援,但曾国荃志不在此,而是一心想要攻克天京,立下不世之功。
于是,东援的重任落到了曾国藩的学生——李鸿章头上。
▲李鸿章。图源:网络
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,跟曾国藩是科举同年。曾国藩在湖南练兵时,李文安、李鸿章父子在安徽办团练。1859年,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军中。曾国藩有意雕琢这位年轻人。他有一个习惯,每天黎明必召幕僚一起吃饭,李鸿章遭受不住,便说自己头痛,起不来。曾国藩十分生气,“必待幕僚到齐乃食”。李鸿章只好披着衣服,狼狈赶来。餐桌上,曾国藩不发一言,吃完饭后,才严肃说道:“少荃(李鸿章),既入我幕,我有言相告,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。”
李鸿章时常和曾国藩发生争吵。在祁门时,他就提醒过老师,此地乃兵家绝地,不如移军别处。曾国藩不听,他据理力争,气得曾国藩骂道:“诸君如胆怯,可各散去。”
之后,曾国藩的患难久从之将李元度在徽州大败,临阵脱逃。曾国藩一气之下,不顾多年情谊,要参劾李元度。湘军上下都认为曾“过激”,反对弹劾。李鸿章极力劝道:“果必奏劾,门生不敢拟稿。”曾国藩不吃这一套:“我自属稿。”李鸿章又说:“若此,则门生亦将告辞,不能留侍矣。”曾还是不为所动:“听君之便。”
结果,李鸿章赌气离去,在江西赋闲将近一年。1861年6月,曾国藩写信给他,邀其“速来相助”,李鸿章就坡上驴,欣然前往。重入幕府后,李鸿章渐掌兵事。冬天,曾国藩酝酿安排曾国荃去上海时,明确表示让李鸿章同去。既然曾国荃不想去,那么统帅一职非李鸿章莫属。
1862年初,李鸿章开始组建淮军。他早年与父亲在家乡办团练,与淮勇头目如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吴长庆、刘铭传等人相熟。有湘军开创的体制在先,又有早已成型的部队,只需要挑强汰弱,便轻松募得四营——树字营(长官张树声)、铭字营(长官刘铭传)、鼎字营(长官潘鼎新)、庆字营(长官吴长庆)。
3月,淮勇在安庆集结,接受曾国藩的检阅。曾国藩觉得淮军人数太少,战斗经验不足,又调拨了九个营:曾国藩的两个亲兵营,开字两营,林字两营,以及熊字营、垣字营、春字营。开字营的长官是程学启,安徽人,本是太平军将领,在湘军攻下安庆前夕倒戈。春字营长官张遇春,最初隶属于李鸿章办的团练,后编入湘军,历时数年,如今回归淮军。剩下几个营的长官,全都是湖南人。正如史学家罗尔纲所言:“淮军与湘军,犹如儿子与母亲,曾国藩与淮军,犹如老褓母与婴儿。”
经过补充之后,淮军共十三营,每营500人,共6500名士兵。算上民夫,总人数达9000余人。
▲淮军名将刘铭传。图源:网络
4月8日,李鸿章搭船抵达上海。不出一个月,朝廷任命他为江苏巡抚的旨意就下来了。上海的局势十分复杂,华、洋势力杂处其中。曾国藩的政敌、原江苏巡抚薛焕虽已卸任,但仍管理着东南沿海的通商事务,隶属于总理衙门。曾国藩不敢贸然对其动手,怕惹到背后的大人物——奕䜣。薛焕的亲信吴煦掌管着上海的财政大权,控制着每年近200万两的收入,还雇佣了一支洋枪队。
吴煦在1860年之前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僚,没有什么背景。他能够在江苏官场步步高升、稳坐泰山,在于三点:会理财,掌握一支洋枪队,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。
李鸿章到上海之后,并未立马清算江浙官场,而是先稳住吴煦,然后暗地里削弱他的权柄。首先,李鸿章派手下接管厘捐总局,派吴煦去管海关,之后又派人接替吴煦“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事务”一职,让吴煦成为空头的江苏布政使——反正布政使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。由此,李鸿章掌握了关税和厘金这两棵摇钱树。其次,李鸿章亲自出面与外国人交涉,试探一番后惊喜地发现:外国人虽然与吴煦有私交,但也有抱怨,只要能满足列强的要求,他们并不在乎和谁谈。到头来,吴煦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:洋枪队。
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承关系,淮军也是湘军的翻版。然而,踏上上海这方土地后,他们就已经走上一条不同的路了。
李鸿章起家翰林,浸淫儒术多年,但还没有等到摸到门径,就带兵去了。曾国藩用他,也是看重他一手奏折功夫。后来的生涯里,李鸿章以办事的能力闻名天下,而义理、辞章、考据等等,终成陌路。
面对天下变局,一个富有情怀的人会去琢磨世道人心——正如曾国藩写下《讨粤匪檄》,继而投身于剿灭叛军的事业之中。立言、立功、立德,这是两千年来大儒当为之事。哪怕曾国藩十分怀疑清王朝的气数,常常怀有一种黑云压城、无可阻挡的悲凉之念,也要拼命卫“道”。相比之下,李鸿章既有忧患意识,亦有扭转时局的气魄,只是所思所想的东西都非常具体:兵事、外交、西方器物……
李鸿章经营上海,所做之事与吴煦没有多大差别。第一,他控制了上海的税源,获得了大量的军费。第二,他将淮军改造成一支使用洋枪洋炮、采用洋操训练、有军事工业支撑的军队。第三,他不断精进自己的外交本领,并与总理衙门对接,在1863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。那一年,他奏请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,开启了漫长的洋务生涯。实业、实利、实功,这是新时代变法者的执着。
李鸿章创立淮军,招募将帅,首重能力,“文章道德,尚在其次”。到上海后,又召集了一帮洋务人才,专业性极强,信念感不多,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。如果说早期的湘军将领靠一个古老的理想凝聚在一起,那么驱使淮军人物(包括后面的北洋人物)的更多是“利禄”二字。终其一生,李鸿章都摆脱不了“小人爱利”这个标签,走到哪里,都会有人站在君子的角度审判他。
曾国藩一开始看不上洋枪洋炮,认为军力强弱取决于人,而非兵器。见识过“轮船之速、枪炮之远”后,他不得不产生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想法。攻下安庆仅三个月后,他就设安庆内军械所,尝试制造蒸汽机、轮船和枪炮。
不过,他始终留恋着世道人心。他曾目睹西洋千里镜,感慨仪器之精妙,却引发了一段另类的思考:“因思天下凡物,加倍磨冶皆能变换本质,别生精彩,何况人之于学?但能日新又新,百倍其功,何患不变化气质,超凡入圣?”于他而言,万事万物终究还是要回到道德之中。而李鸿章却说:“孔子不会打洋枪,今不足贵也。”
两人性格的差异,造就了湘淮系不同的命运。
21862年初,英法联军出动,炮轰宁波,进攻太平军。接着,他们联合吴煦手下的洋枪队大举进攻上海周边的太平军据点。
这支洋枪队名为常胜军,建立于1860年。其首领华尔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亡命之徒,出身水手世家,接受过军事教育,热爱冒险,渴望战争。而江浙官场与湘军不同,严守文武分途的体制:文官可以通过粮饷的供给驱使武官去做事,但不会直接带兵。双方一拍即合,由吴煦、杨坊出面雇佣华尔的常胜军。
常胜军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武器和战术,但与太平军交战多次,难求一胜。1861年末,华尔重建了常胜军,总算有了像样的战力。
▲华尔。图源:网络
李鸿章来到上海之后,很快意识到“目前之患在于寇,长久之患在西人”,自强的念头已经萌芽。他虽然要和洋人合作剿贼,却不愿意他们插手军务。换言之,洋人最好别介入战争,如果非要介入,直接出兵可以,训练、指挥中国军队不行。华尔虽是美国人,名义上却听吴煦等人指挥,也是李鸿章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。于是英国人转而与华尔结盟,以减轻操纵中国军事力量的嫌疑。英国人不仅为常胜军提供榴弹炮、滑膛枪、军服等物资,还安排英法联军配合常胜军作战。
天时地利人和俱在,常胜军久违地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。然而,太平军主力一杀来,英法联军和常胜军立马遭遇惨败。要不是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,调走了最精锐的部队,常胜军恐怕难以立足。
血染红了上海城内外。城外,各方势力相互厮杀,然后不约而同一起洗劫老百姓。城内,太平军俘虏遭到了极为血腥的处决——当然,这是西方人的看法,中国人十分明白叛军会得到怎样的下场。一些英国人看不下去,谴责本国的虚伪嘴脸。他们认为英法两国介入战争,是支持行将就木的清王朝,以进行殖民扩张。曾翻译四书五经的汉学家理雅各就说:“我们会在战场上杀掉数千人,而诸省巡抚会在刑场杀掉数万人……我们的高阶军官将会效命于许多杀人屠夫。”
一部分英国人确实拥有强烈的正义感。但归根到底,这些人考虑的是英国的最大利益,至于这些利益到底是什么,他们的看法不总是完全一致。那些反对战争的人很难意识到,他们口中常常念叨的“贸易”“文明”和“福音”,同样是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欺凌。由于内部的不统一,在整个清朝内战期间,英国一下子强硬,一下子又讲道理;一下子中立,一下子又替人打仗;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,一下子又痛斥它。
最有原则的英国人是军火商:谁给钱,谁就是朋友。太平军夺下宁波之后,“大炮成百地,枪支成千地,弹药成吨地进口宁波港”。清政府像个怨妇一样抱怨,开放长江本是为了通商,反而资助了太平军。要不是军火过于昂贵,太平军的战力还要再上一层楼。据参加太平军的英人马惇说:“苏州城中可能有三万支外国枪,叛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福枪,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带来福。”
1862年9月,一名太平军战士用一颗来自外国的子弹击中了华尔,终结了这个亡命之徒的一生。常胜军由华尔的副手白齐文(美国人)接任。整个秋天,淮军与常胜军相互配合,肃清了上海周边的叛军势力。李鸿章派常胜军去支援曾国荃,吴煦、杨坊欣然同意,但白齐文不干了。去天京十有八九是找死,还不如在上海周边打家劫舍。杨坊以扣押军饷威胁白齐文,白齐文回到上海,跑到杨坊家里,将其打伤,抢走了洋银四万余元。
事发之后,李鸿章宣布解除白齐文的职务,悬赏五万两猎取他的人头,还找来英国人,要求他们找一个靠谱的人担任常胜军军官,同时削减外籍军官的权限。之后,他把常胜军的一堆烂账推给吴煦、杨坊,迫使其下台、赔钱。至此,吴煦彻底出局。
英国人戈登接下了常胜军的担子。他出身军官世家,背负着荣誉和责任,内心极为鄙视雇佣军之行径。上任之后,他把常胜军好好地整顿了一番,并得到了英国更多的援助。为补充兵员,他收编了许多太平军战士。此举招致李鸿章的强烈反对,可戈登根本不在乎。他曾哀悼为他作战牺牲的太平军战士:“他们打起仗了像魔鬼一样,却令人悲痛地死去了。……这或许正是对他们过去罪孽的回应。”
▲戈登。图源:网络
这样一个荣誉至上的愣头青出现在江南战场是非常违和的,但他确实能打胜仗。1863年夏,常胜军与淮军联合作战,陆续攻下常熟、太仓、昆山、吴江、江阴等地,11月中旬开始进攻苏州。苏州城守将、慕王谭绍光率军浴血奋战,打退了联军一次又一次进攻。到了这时,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太平军能取得胜利了。苏州城内有八位等级略低的王不愿与太平天国陪葬,秘密和联军联系,打算献城投降。戈登说,只要能以最少伤亡拿下苏州城,他愿意保护降将的安全。12月4日,八王割下谭绍光首级,大开城门,迎接淮军进城。随后,戈登入城,会见八王,欲提供保护,八王劝其不用担心,还答应调千名士兵补充常胜军。
12月6日,李鸿章接管苏州,情势生变。诸王自恃投诚有功,索要兵马和官职,并要求驻守“苏州之半”。李鸿章并非有功不赏、过河拆桥之人——按照淮军对待投诚者的惯例,如果八王归顺后奋勇杀敌,他自会为其请赏。可是,八王既然如此要挟,那就只能迎来屠刀。很快,苏州城“一声炮响,四起杀声”,戈登心知不妙,向淮军要人,只看到了被肢解的尸体。数万太平军俘虏惨遭屠戮,尸体甚至阻滞了轮船的行驶。曾国藩得知苏州杀降后,欣然称道:“此间近事,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。”
戈登内心的正义被人无情践踏,怒火直冲云霄,直接拒绝了清廷的赏赐,还扬言要打清军。苏州杀降一事公开后,部分英国人仿佛惊觉一个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:他们从来不是什么文明之光,而是“人道灾难的制造者”(这个称号一直用在太平军身上)。他们要求立马停止对清朝的援助。也有聪明人看出,如果英国要维持对华贸易,不可避免要杀人流血,甚至直接出兵征服中国。既然是为了利益,就不要装出一副伪善的面目了。
然而,搞政治就必须要装样子。英国议会重拾中立政策,宣布不再参与上海之外的战事。李鸿章深谙以退为进的官场哲学,上奏称如破坏“中外和好”大局,就请从严治罪,给英国人一个说法。皇帝回答了一句:“洋人不明事理。”之后,英国人又开始担忧起丝绸的贸易,人道焦虑早已抛之脑后。常胜军按兵不动,又有腐化的迹象。李鸿章找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,从中调停。大势压来,一名英国军官的小小骄傲简直不值一提。
▲赫德。图源:网络
1864 年2月1日,李鸿章、戈登和赫德在苏州会晤。李鸿章发布告示说明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,戈登同意常胜军于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出战。
对外交涉中,李鸿章渐渐摸到了门道。洋人不是洪水猛兽,只要是人,总会被制度所限制,总会有派系之别,总要讲人情世故。对待外国人,不必太过谄媚,不必太过强硬,用他的话说,“鸿章以孤军与方外杂处,每至十分饶舌,用痞子放赖手段,彼亦无如之何。其顺情理,则以情理待之,其不顺情理,则以不顺情理待之。”这些都是曾国藩、左宗棠所缺乏,后来也没有机会弥补的手段。
1863年之后,淮军的武力、江浙的财力、总理衙门的支持、自强的理念,最终结合成一个庞大的权力结构。其名为“洋务”。
3视线拉回天京的战场。
1862年春,李鸿章与淮军赴上海的同时,湘军主力向皖北推进。
陈玉成在安庆之战后,发兵向河南和陕西进军,但自己却被多隆阿的骑兵缠上,困在庐州。离他最近的友军是寿州的苗沛霖部——这是一支地方乱军,投过捻军,降过清,也依附过太平军。此时,苗沛霖再次降清,为了保住人头,答应清军诱捕陈玉成。
陈玉成应苗沛霖的邀请,率部从庐州杀出,准备与其会合。他刚进寿州城门,就被苗沛霖的伏兵擒下,随后被送往颍州,接受审讯。他在死前感叹道:“太平天国去我一人,江山也算去了一半!”随后被清廷凌迟处死。
▲陈玉成。图源:影视剧照
当时,左宗棠的楚军进攻浙江,李鸿章的淮军和英法联军进攻江苏,使得李秀成将主力调往江浙。摆在曾国荃面前的是一片坦途。很快,他率领两万人来到了天京城外的一座小山前。此山是一个军事要塞,名叫雨花台。他并不着急,而是像往常一样筑营寨、挖壕沟,慢慢吞下比自己多数倍的守军。
夏天,江南爆发大规模霍乱。从南京城外的军营,一直蔓延到上海的难民营,只要是拥挤的地方,遍地都是发臭的尸体。曾国荃部有万人病倒,占围城兵力的一半;鲍超的霆军也有万人染疫;左宗棠部的感染率达到五成。湘军已无力主动出击。
秋天,李秀成率十余万主力回援天京,亲自攻打曾国荃的营垒。曾国荃几乎没有援军,鲍超陷于皖南,多隆阿跑去陕西平回乱。曾国藩劝他撤军,曾国荃不肯。一旦离开前线,攻克南京的功劳可能就要归于别人,他必须牢牢占住这个位置。
猛攻很快开始,太平军的炮弹如雨点一般落入湘军的阵地之中。幸亏曾国荃扎营结寨的功夫太硬,无论是炮轰、冲锋、挖地道,都不能撼动湘军防线分毫。然而,李秀成不缺人,也不缺军火,只要有一波没守住,曾国荃就要完蛋。
某日,一枚炮弹的碎片划伤了曾国荃,但只是皮肉伤,未危及生命。
曾国藩身在安庆,夜不能寐,为弟弟担忧。他找上李鸿章,要他支援曾国荃,李鸿章提出派遣常胜军。曾国藩曾多次反对洋佣兵助剿,此刻也顾不上了,同意了这份提议。凛冬将至,他再次写信给弟弟,要他退到安全的地方。
但曾国荃坚守不退。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挑战着湘军的士气。所幸,他们撑住了。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猛攻之后,李秀成停止了进攻。由于长江被湘军水师占据,李秀成部要想获得粮草,要么靠天京接济,要么靠苏州陆运过来。天京城有三十万张吃饭的嘴,不可能供应他。苏州太远,缓不济急。李秀成无奈,选择了退兵。
对于这场胜利,曾国藩丝毫不觉欣喜。太平军兵力多,完全可以重振旗鼓,但曾国荃的兵马要是拼完了,就彻底输了。当然,他的判断错了。太平军已经完全陷入颓势之中了。左宗棠和李鸿章收复江浙失地,有力地牵制了李秀成的部队,迫使其四处作战。天京城内粮草短缺,人心浮动,太平军战力急剧下降。曾国荃一心一意围天京,看似呆板,其实切中了要害。
1863年夏天,曾国荃终于攻下了雨花台的要塞。从山上俯瞰天京城,正如一头疲惫的困兽。接下来,曾国荃将城外的关隘和桥梁一一拔除,几乎封锁了天京所有的出路。
1863年末,李鸿章攻克苏州,李秀成回到天京,劝说洪秀全放弃京城,转进江西。此时的洪秀全完全没有决断力,坚决不肯。李秀成没有放弃太平天国,留下来督兵死守。洪仁玕也没有放弃,出天京招募兵员,但响应者寥寥——已经没有多少人对太平天国有信心了。
此时,曾国荃部也是问题重重,粮食短缺,纪律全无,很快就撑不下去了。清廷想把淮军调来参战,但曾国荃怎么可能同意?李鸿章顾及私人情谊,借口淮军要攻打别处,一再拖延,给曾国荃争取时间。曾国藩也急了,给弟弟写信道:“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?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?”
曾国荃迫于形势,不顾伤亡,命令士兵冲锋。1864年7月19日,湘军攻破天京,冲进天王宫,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。洪秀全早在6月1日就去世了,幼天王也不见踪影。原来李秀成带着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,借着夜色的掩护,护卫幼天王突围出去了。李秀成舍命冲锋,与队伍分散,来到城郊一处乡庙暂避风头。两个乡民识破李秀成的身份,将其擒住,送往清营。由于没有抓到幼天王,曾国藩为了战功好看一些,谎称其已经自焚而死。
湘军破城之后,释放了内心的野兽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南京城陷入火海,好似一个炼狱。7月19日,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请求曾国荃“止杀”,曾国荃不许,宣布驰禁三日。7月25日,赵烈文进入南京,惊诧于所见景象:“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,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皆斫戮以为戏,匍匐道上。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。老者无不负伤,或十余刀、数十刀,哀号之声达于四远,其乱如此,可为发指。”士兵对平民严刑拷打,逼他们说出太平军藏宝的地点,有力气的人替他们搬运财物,病人和老弱则直接处死。
历史也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女子惨痛的遭遇。她叫黄淑华,十六岁。湘军上门时,砍死了她的二兄。一位壮汉抓住了她,她的弟弟牵着壮汉的衣服,母亲也跪下求情,壮汉大怒道:“从贼者,杀无赦,主帅令也。汝不闻也?”于是杀掉了她的弟弟和母亲。她的长嫂又过来求情,一同被砍翻。黄淑华悲痛欲绝,想要寻死,但被壮汉拉住,那壮汉说,我爱你,我不杀你。之后,壮汉打算把她掳回湖南。途中,黄淑华在纸帛上写下自己的遭遇,一张贴在客栈的墙上,一张贴身藏着,趁壮汉不备,将其杀死,然后上吊自杀。后来,当地人将这个故事写入《湘乡志》的《烈女传》。
▲《克复金陵图》。图源:网络
李秀成被俘一星期后,曾国荃就用酷刑撬开了他的嘴。7月28日,曾国藩来到南京,逼李秀成写下了数万字的口供,并删除口供中对湘军不利的部分,重新誊抄一遍,印成《李秀成供》。曾国藩一直不肯将李秀成的手迹公之于众,直到1944年才有人在曾家故宅发现这一秘本。
在口供中,李秀成流露出求饶之意,称“我见老中堂(曾国藩)大义恩深,实大鸿才,心悔莫及”,还说“今天国已亡,实大清皇上之福德,万幸之至”。不难看出,李秀成多少有些贪生的念头。赵烈文隐约觉察出李秀成“言次有乞活之意”,对他说:“汝罪大,当听中旨,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。”恐怕曾国藩利用了李秀成的求生欲,对他有所许诺,才让其写下了这些口供。
8月3日,曾国藩对赵烈文说,他打算先斩后奏,处决李秀成。他心里清楚,朝廷多半会要他将李秀成活着押送京城,而李秀成为了活命,必然会拉曾国藩下水,将湘军的一些丑事全都说出去。
8月7日,曾国藩果断将李秀成处死。
另一边,洪仁玕得知幼天王出走的消息,将其迎入广德,准备开赴江西。洪仁玕的计划,是与太平军残部会合,取道湖北,进军陕西,再举大业。然而,清军追得太凶,两人先后被捕。
临死之前,洪仁玕读到了李秀成的供词,骂他“变更不一,多有贻误”。他不肯向清朝屈膝,说自己“志在攘夷愿未酬”,随后英勇就义。
4湘军攻下天京的那一刻,既是曾国藩权势的顶点,也是他衰落的开始。
左宗棠上奏揭露曾国藩谎报幼天王已死的军情,湘系内部的裂隙进一步扩大。北京大肆宣传湘军烧杀抢掠的行径,利用清议打击曾国藩兄弟的威望。曾国藩四面受敌,流露出忧惧之意。他给曾国荃写信道:“阿兄忝窃高位,又窃虚名,时时有颠坠之虞。吾通阅古今人物,似此名位权势,能保全善终者极少。”统治着半个中国的人,竟然会如此忧心忡忡。
内在的曾国藩,就是一个传统的儒生。他可以为了保卫孔子之道而疯狂杀人,也可以痛骂腐败的朝廷、无能的官僚,但不会想自立当皇帝。权力令人感到害怕,甚至不如故纸堆吸引人。他最终选择了消极自保,让出兵权,以保住盖世英名和身家性命。
攻下天京后第十九天,曾国藩上《粗筹善后事宜折》指出:“臣统军太多,即拟裁撤三四万人。”当然,曾国藩裁军还有一层考虑:湘军已是强弩之末,粮饷拖欠已久,将帅志骄意惰,兵士掳掠成性,如不裁撤,必是一大祸害。
当时在江南地区的军队主要有三部分:一是江苏李鸿章部淮军,大约七万余人;二是浙江左宗棠楚军,近五万人;三是曾国荃部五万余人,加上曾国藩大营和鲍超等部,总兵力约有十余万人。
曾国藩觉得淮军更有战斗力,与李鸿章商议,表明了“裁湘留淮”的意愿。对于曾国藩的决定,李鸿章自然是同意的。不过,淮军未必有多好。李鸿章透露,“三年以来,统计欠饷已达七八百万两”,淮军基本也靠掳掠来维持士气。因此,他提议淮军只留三万人,以防备虎视眈眈的外国人。
从1864年秋到1865年初夏,曾国藩分批裁掉了约六万人。裁军需要大量银钱,以补齐欠饷、支付遣散费用。许多湘军士兵得不到应有的待遇,只能闹事。1865年5月,战力很强、但军纪奇差的“霆军”突然闹饷,一处生变,各地效仿,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福建均有兵营哗变之事。曾国藩叫来正在养病的鲍超,安抚霆军将士,然后拼凑钱粮,放缓裁军的脚步。到了1866年,除了“霆军”之外,湘军基本只剩下老湘营6000人(其中3000人是新兵)。后来,霆军被打散,有的进了淮军,有的进了左宗棠部。老湘营也随左宗棠去了西北。
▲鲍超画像。图源:网络
1865年,负责剿灭捻军的僧格林沁被击毙,清廷征召曾国藩剿捻。朝廷并不想用曾国藩,但以他的声望和地位,又不能不重用。湘军次第被裁,曾国藩只能率领淮军剿捻。出征之前,李鸿章非常担心老师此行的结果:“节相奉命讨贼,义不容辞,惟部下已乏强兵,精力亦甚疲惫,勉起就道,未知能否终局。”
果然,曾国藩北上不久,屡屡碰壁。要说淮军内部排挤他,是谈不上的。他突然来到中原剿匪,不熟悉形势,回到了四面堵截的老办法——对付太平军还算有用,对付捻军则不行。他也不熟悉各地长官和部下,做事难免受他人掣肘。清廷失去了耐心,中途换帅,让李鸿章走马上任。1869年,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,再度陷入困境,又是李鸿章替他擦屁股。
湘消淮长、曾李交替虽是清廷有意为之,但也和曾国藩跟不上时代有关系。他开创了新的体制,建立了湘军,带出了成批的疆吏,成立了无数以“局”命名的机构。可一旦脱离了战争,他的视野还是回到了儒家那一套东西里。
相较之下,左宗棠算是半只脚跨入了新时代。
1863年初,左宗棠向总理衙门建议,仿造轮船,以备海防。1866年,他创办福州船政局。随后,被任命为陕甘总督,不得不从沿海走向内地。他花了七年时间平息回乱,又遇到俄国人入侵新疆,他的人生重心不再是海防,而是塞防。由于多年身处边疆,他与蓬勃发展的洋务运动已经有了一层深深的隔膜。1881年,他功成回京、入值军机,看起来位高权重,实则沦为慈禧制约李鸿章的一个工具人。
同年10月,左宗棠外放为两江总督,大量任用湖南人。随后,他以患病为由奏请开缺,保举曾国荃为继任者。曾国荃任两江总督近七年,“大招湘军旧部,扩建新营头”。经过湘系多年的经营,终于形成了南洋湘系、北洋淮系的格局。
李鸿章走得最远。
剿捻成功之后,清廷还是想裁淮军,刘铭传、潘鼎新心生退意,纷纷辞官。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时,向朝廷提议,“畿辅要区,为皇都拱卫”,应当规划部队,沿海戒备。于是,淮军顺理成章入驻了直隶。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二十余年,主管洋务、海防、招商三大要务。北洋所在,几乎成为总理衙门之外的又一个政府。等到湘系最后一个大佬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时,以北洋“尽天下之财力”为世间之大不平。
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,其人生劣迹斑斑,但许多人把他当作精神领袖。李鸿章虽是洋务巨擘,却鲜有人视其为导师——他1901年离开人世之时,留下了一堆残破不堪的洋务事业,和一个坏名声。
器物升了值,人格却贬了值。传统和现代之间依然横亘着一道长长的裂痕。
参考文献:
顾廷龙、戴逸主编:《李鸿章全集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8年
樊昕整理:《赵烈文日记》,中华书局,2020年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:《吴煦档案选编》(全7册)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3年
【美】史密斯:《19世纪的中国常胜军: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3年
王尔敏:《淮军志》,中华书局,1987年
杨国强:《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彷徨:曾国藩、李鸿章及其时代》,生活•读书•新知三联书店,2008年
翁飞:《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》,《军事历史研究》,2011年第3期
王瑞成:《“权力外移”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(1855—1875)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,2012年第2期
顾建娣:《曾国藩对湘军陆师的裁撤与安置》,《军事历史研究》,2019年第4期
发布于:广东省实盘杠杆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